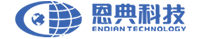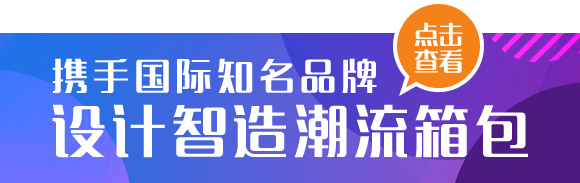93岁的刘经传最终未能从深度昏迷中苏醒过来。这位中国一汽咨询委员会委员,原一汽解放联营公司常务董事、一汽总设计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月30日5时53分在长春逝世。中国一汽办公室、党群工作部在讣告中表示,遵照刘经传同志生前遗嘱,丧事从简。
刘经传有着丰富的汽车人生。他是当年一汽制造东风和红旗轿车的重要人员,也是东风轿车处女航中唯一乘客,还是第一辆红旗轿车液压自动变速箱的负责人。
1930年,刘经传出生在江苏仪征,在战争年代度过颠沛流离的童年。1948年参加高考,他填报了3所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武汉大学。结果,他在这3所大学均榜上有名,因向往清华大学,他不顾家人劝阻,选择清华大学电机系,后转念机械系。
1951年,刘经传随所在班级60多位同学一起,被抽调到汽车工业筹备组实习,为建设一汽做准备。1952年毕业,他被分配到汽车工业筹备组。1953年1月,作为一汽“第零批实习生”,他被派到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实习,是一汽设计处来实习的第一人。
1954年,刘经传回国,被分到一汽设计处。他从一名技术员干起,历任设计科副科长、科长,设计处副处长、处长,一汽副总工程师,一汽总设计师,一汽汽研所所长,一汽解放联营公司总工程师和一汽集团常务董事。
在一汽3年建厂出车阶段,他在消化吸收苏联设计文件资料、配合零部件生产调试、外协件选点和试验鉴定方面起到及其重要的作用。担任越野车主管设计师时,他在越野车改进并大批量装备部队中立下汗马功劳。
此外,他还在解放换型开发、解放变型车开发、延长老解放牌寿命,以及制定解放汽车系列新产品型谱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刘经传生前曾多次接受口述历史访谈。2008年5月13日下午,他在长春寓所第一次为我们讲述如何在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用手工敲打出东风和红旗轿车的故事,时长5个多小时。
2018年5月26日上午、27日上午和下午,同样在长春寓所,刘经传再次接受口述访谈,分3次为我们还原其鲜为人知的汽车生涯,时长12个小时。他的讲述,为跌宕起伏的中国汽车工业留下弥足珍贵的史料。
今年时逢中国汽车工业70周年,帮宁工作室谨以本文,向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汽车人告别,向中国汽车工业第一代创业者致敬。本文收录于《解放:中国第一个汽车品牌的前世今生》一书,原国家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作序,中国工人出版社于2019年3月出版。

我父亲在南京中央大学念商科系,毕业后到上海谋生。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兰格木行,后转到永泰和烟草公司,在那里做秘书兼英语翻译。1930年,我在江苏出生。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父亲英语非常好,能直接跟外国人交流,他对我影响较大。
1948年,我参加高考,填报了三所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武汉大学。这三所大学都录取了我。父母不希望我去清华大学,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夕,社会动荡不安,当时京沪铁路已中断,他们都以为离家太远,将来联系会有问题。
但我向往清华大学,向往北方,觉得清华大学空气自由。我的一个姐姐在保险公司工作,是地下党;另一个姐姐结婚后,跟着家人去了台湾;妹妹还在上海上学。父母虽舍不得,但我坚持要去清华大学,他们也没办法。
当时上海到北京的交通只有海运,大姐送我到黄浦江坐轮船。第一天遇到大风,船不能起航。第二天又去,登船后,经过黄海、渤海,进入天津大沽港,然后进入海河,我上岸坐火车到北京。
我考的是清华大学电机系。一段时间后,我感觉电机系功课繁重,得肺病的同学较多,便申请转到机械系。清华大学确实比较自由,有民主墙,也有社团活动。社团很活跃,大多数都由地下党组织。
起初,我还能和家里保持通信,但到了1948年11月,强行进入清华大学,架起三尊炮,其中一尊以我们宿舍为掩体,交通和通信就完全中断了。有几个上海同学在交通中断前回去了,我不想回去,就留在了清华大学。当时想法很简单,就想见见世面。
包围北京城后,双方进行谈判。我们住在清华大学的善斋,能听到外面的枪声。炮兵撤掉后,以机械系教授钱伟长为首,组织了护校队,我也去参加了。护校队在夜里轮流巡视,围着清华园绕一圈。
护校时,我们在机械系的一楼打地铺,晚上起来巡逻,天气很冷,包括钱伟长在内的教授就轮流接待我们。轮到哪家接待,就煮一锅粥给我们喝,再吃些点心。
钱伟长是火箭专家,每次到他家里,他就跟我们讲火箭。那时候火箭还叫“rocket”,他就讲“rocket”怎样怎样,讲得很起劲。钱伟长还教我们材料力学,我成绩非常好,他们都说我是钱伟长的得意门生。
后来枪声渐渐小了,清华大学解放,退守城内,接管清华大学。我出于好奇,翻到墙外去看战场。去墙外的同学从战场上捡回好多,还有一箱一箱的迫击炮弹。按规定,要回收这些武器,并堆放在大操场上烧掉。
接管清华大学后,并未进校。护校结束后,我们就在校园里自由自在地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搬回善斋,老师已经走了不少,课也停了。校委会开始组织宣传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段时间后,有个团长带着警卫员,骑马来到清华园。同学们都很好奇,想看看长什么样。
团长戴着东北大皮帽子,借机发表演讲,讲国内形势,也讲的方针政策。但我当时并不完全明白讲话内容,只是觉得很亲近,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有一天,我们得到消息,说要来清华大学,我们就聚集在操场上。领导来的可真不少,有、彭真、艾思奇等。艾思奇给我们讲辩证唯物主义,讲社会发展史。陈毅也来过,他在大操场上给我们讲全国形势。
学校地下党也组织学生进城宣传,每个人手里都拿一面旗帜,给老百姓讲党的政策。我也跟着进了城,随的装甲车和坦克,经过前门接受检阅。
教授们也很活跃。我记得有个夏天的夜晚,哲学家冯友兰把同学们聚集到操场上,讲蟾宫折桂的故事,他实际是在讲哲学。还有机械系教授宋镜瀛、物理学家钱三强等都来讲课。钱三强讲原子能,华罗庚讲统筹法等,使我们受益匪浅。
学校恢复秩序后,彭珮云代表清华大学校委会讲话,宣布学校复课,但宣传活动还是很多,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农村做宣传时,我被查出患有肝炎,大夫说没有好办法,只有新中国成立前留下来的一些药粉可以溶解成针剂,但都过期了,问我打不打。
我同意打。当时营养品很少,天天吃白薯和红山芋。大夫叮嘱我不能吃油,所以我不敢进食堂,只能到饭店要一碗没有油的鸡蛋面条,慢慢养好身体。
我跟家里恢复了联系。上海还没解放时,大姐去了苏北解放区,她给我写过信。我把大姐寄来的信,封在我的信里寄回家。后来才知道,这样寄信很危险,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对防范严密,大姐原来在上海,正为将来接管上海做准备。
1951年我念大三,开始上像内燃机这样的专业课。我成绩一直比较好,还给别人辅导功课。有个地下党被派到解放区,回来后课程跟不上,我就辅导他。
当时,中苏已经签订了148项援助协议,其中一项就是要建一个汽车厂,于是重工业部就成立了汽车工业筹备组。当时筹备组副组长是孟少农,他是汽车技术权威人士。他认为,汽车工业相当复杂,需要大量人才,所以筹备组的第一件事就是培养人才。
于是筹备组就提出,要从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工学院和东北工学院等学校招人。1951年7月,筹备组到这些大学里去动员大三学生,表示学校实行教育改革,可以先到筹备组实习一年,下工厂锻炼,再回来念大四。
我们被当作未来汽车工程技术人员培养,为将来建一汽做准备。我所在班级有80多人,其中2/3的同学被抽调到筹备组。我们分别被派到上海、天津、北京等地较大的工厂实习。
我被派到天津汽车制配厂(天津拖拉机厂前身)实习,这个厂有800人,厂长是个团长,大家都叫他“李麻子”。我在这里实习了三个月,铸造、钳工、车床、机床等各个工种都学。
在这期间,我认识了李刚,知道他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当时是车工部主任。实习到车工组时,他教我们车床,还有工具、刀具等操作知识,还让老师傅带着我,加工一个双拐小曲轴。谁知加工到最后,曲轴中间一下就断了,这是实训。
天津汽车制配厂知道中国将来要造汽车,而且要建一个大汽车厂。这时,制配厂独立做出一款小发动机。他们都以为,能做发动机就能造汽车,因此要造中国第一辆汽车。
于是,他们开始设计图纸,让钣金工按照图样敲出一个车壳子。设计图样的是吕彦斌,他后来去了一汽。他们拿来美制吉普车的底盘,配上自己做的四缸发动机,做出两辆样车,一辆是钣金工按照图样敲的,另一辆相当于小旅行车。
我在制作的步骤中也作了贡献。原本齿轮应该用机器加工,但当时机器质量不好,只好用手工做,但做出来的齿轮齿子肥大,我们就挨个把它锉瘦,直到检查通过。他们装出车到北京献礼,受到朱德总司令接见。这两辆车做成后引起了轰动,还在报纸上作了宣传。

实习回来后,我被安排到南池子试验室实习。试验室隶属汽车工业筹备组,聚集着全国有名的机械业专家,实习生分别来自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山东工学院、河北工学院、沈阳工学院等,加起来有近百人。
试验室下设设计室、加工车间、精工、材料等科室,主任是吴敬业。他热情地接待我们,并勉励我们说:“别看我们现在人少,也没太多装备,你们在这里好好学习,将来汽车工业就要靠你们这批人了。”
我被分到设计室,负责人是张世英。我的主要工作是为天津汽车制配厂制图,也就是测绘苏联的嘎斯69越野车。这次测绘比较正规,要挨个测绘每个零件。
分工时,我被分到底盘后桥组,主要负责设计后桥伞齿轮,也就是格力森这一套机器。这时,蔡传平要求加入设计组,他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认为设计螺旋伞齿轮是高级技术活,很有兴趣。张世英就让他代替了我的位置。
我被调去测绘嘎斯69越野车的车架大梁。当时没有人知道如何测量,只能自己想办法。我就在试验室找到一块水磨石地,把它作为平板,拿线一点一点地吊,大梁是三维,弯弯曲曲的形状,我就依据尺寸画出大梁。
实习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将汽车解体。1951年夏天,我们100多名大学生被集中到位于东四北大街的北京中法大学(1950年,其本部及数理化等院系并入北京工业学院,1988年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大操场上,筹备组提供了两辆车,一辆吉斯150,一辆美国中吉普。
筹备组让我们对汽车进行解体,并安排比我们高两届的学长以及开这两辆车的老师傅作为导师,让我们有不懂的地方就向他们请教。拆变速箱里的同步器时,我还问这零件干什么用?沈同文(后来去了二汽)说,“你自己琢磨,琢磨完了再解答”。当时的教育学生的方式就是这样的。我还真琢磨出来了,同步器是起同步作用的。沈同文说,“对了”。
我们把汽车拆完,再组装起来,大概用了一个月时间。这期间,老师傅帮着我们作调整。组装完成后,汽车一启动,还能走。拆散、组装、启动、开走,这堂课很有意义,比学校里教的汽车构造要深刻得多。
最后,老师傅还教我们开中吉普车。学车的地方在老广场,正对着紫禁城的地方,当时只有大红墙,人民大会堂还没有建。我们一次学半小时,共学了八次,就从不会开车到能开着车钻杆的水平,这同样也是实践教学法。
一年实习期结束后,我们等着回校继续念大四。这期间的一天,汽车工业筹备组的老通知我们到中法大学礼堂开会。老胳膊下经常夹着一个皮包,说一口四川话。他上来讲的第一句就是:“你们别走了,都留下。”我们听得莫名其妙。他接着说:“你们不回学校了,就留在筹备组。”我们当时也没觉得太震惊,只是觉得要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后来,学校为我们颁发了毕业证书。同学们被分到洛阳轴承厂、洛阳拖拉机厂、机车厂等地。筹备组留下了七八十人,接着再分配,我和另外七人被分到教育处。
我们住在崇文门的一个四合院里,开会和吃饭都在扁担厂,交通工具是一辆中吉普。上面安排我们先学俄语,给每人发了一本清华大学的俄文速成课本,但教材没有讲发音。
筹备组有个叫江朝西的老工程师,他说他懂八国语言,可以教我们俄语。其实他对俄语不太懂,发音蹩脚,文法也不通。我们就向筹备组教育处反映情况,让江朝西停止授课。后来我们就开始自学,稀里糊涂地背俄文单词,发音也不标准,读什么的都有。
1951年筹备组主任郭力宣布内容,要在长春建652厂。各位明白建厂地点后都非常兴奋。当年年底,筹备组通知我们八个人,说让我们学俄语是为了去苏联,而且我们将来都要被分到652厂。
接着,筹备组开始给我们置装,每人一套西装、一套中山装,外面有羊皮呢子大衣、一个貂皮帽子、一个普通帽子,还有一副手套。

1952年2月,我们被派到苏联实习,一年后回到一汽,受到饶斌厂长的接待。他热情地跟我们介绍一汽情况,让我们把从苏联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大家。在一汽的资料里,我们被称为最早的实习生,后来有文章说我们是“第零批实习生”。
这时一汽已破土动工。我被分到设计处。设计处约有100人,有设计科、试验室、试制车间、文件科、行政科等科室。设计科和试验室的骨干大多是从南池子试验室调过来的,如叶智、王汝湜、沈同文、蔡传平等,还有从天津调来的吕彦斌、胡同勋等,我都熟悉。
我的工作内容主要有两项。一是给设计处的同事讲课,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对设计处的工作并不太熟悉,我就给他们讲苏联设计处的组织架构、组织分工、工作程序以及管理工作等。
我先在设计处科室讲,然后到一汽其他处室讲,再后来,也到外面其他单位和学校讲。国内的同志对苏联的了解大多来自书本,听我讲的东西感觉很新鲜。
在苏联实习时,我们都攒了些钱,准备买些东西回来。我经常到红场附近的书店买书,主要是产品设计、产品试验方面的书籍。我把这些书都带回一汽,在设计处成立了一个图书馆,朱德照把这些书全部编号,谁要借书就登记。大家都很喜欢这些书,借走后针对专业看内容。
二是翻译带回来的文件。设计处里30多个设计师全部投入图纸翻译工作中。翻译这些图纸时,也遇到了大量问题:有看不懂的地方,我就给他们解释;苏联图纸上有错误的,我就按照苏联的程序,给他们写信,让他们更正。这期间,我建立了设计处流程管理。
翻译图纸要抓紧时间,大家都工作到很晚。有时晚上累了,就在单位打地铺,或者把办公室桌子拼起来睡觉。那时我们住的绿园,是日本人留下来的一些砖瓦平房。房子里没有地板,地面潮湿,箱子放在地上会发霉,夏天还好,冬天得烧火墙。
绿园离我们工作的地方很远,很荒凉,路上没有灯,远处会有野狼,有时都能听到狼嚎,大家晚上都不敢一个人走。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都专注工作,一点都不在乎。
1953年年末,设计处搬到老“皇宫”,我们的办公室是一个小四方的带天井的地方。苏联专家专门有一间办公室,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溥仪登基的地方。
产品设计图纸被称为绝密文件,在孟家屯时由保卫部专门站岗守卫。我们新搬的地方很偏僻,北面基本没什么人。为保卫图纸,夜里我们都出来巡逻,每两个钟头换一次人。睡觉前,我们抽签分配房间,我抽到的是婉容寝室里的小套间,有五六平方米。
1955年,苏联专家到一汽援建。设计处来了一位专家,叫费思达(音译),他是吉斯150卡车总设计师。在苏联实习时,我就跟费思达认识,也在他那里实习过。
一汽对苏联专家非常尊重,派专人负责每个专家的工作。我被指定为费思达的工作人员,相当于他的助手。别人要找他,得由我安排;向他请教的问题,我得做好记录,这些记录还要复印上报,作为正式文件存档。费思达在中国待了两年,我跟着他继续学习了两年。
后来,一汽开始做解放汽车的生产准备工作。第一步是要调试零件,每调试出一个零件就要检查,检查合格后再由苏联设计专家和工艺专家鉴定。我记得调试最早的成品,是由金属品车间生产的气门芯。零件调试出来后,我陪着苏联专家鉴定,检验合格后才能生产。
那时我国技术较落后,有部分外协产品,大概占比30%。外协产品要在中国本土购买,具体选什么配套企业,要当地考验查证,工作量很大。对外协产品的质量发展要求也很高,要符合技术条件,还要做试验,很多工厂都达不到要求。
如当时刹车摩擦片做得最好的是南京的一家公司,他们是用石棉裹着铜丝,然后用树脂压成片,而我们规定汽车上要用压制成型的石棉加树脂。苏联专家很仔细,他们虽然对专业厂不甚了解,但熟悉技术,也知道配方,就让他们按要求做。
这些配件厂也很努力,听说要为中国造汽车,便全力以赴支持,按照图纸要求和苏联专家的提示做。就这样,后来真培养出一批正规的配套厂。
解放投产时,自制零件和国内配套件数量很少。1956年生产的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大部分用的是苏联零件,从苏联运过来,然后生产调试,在总装线上装配,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国产零件,但要说具体用了多少苏联零件,用了多少国产零件,还真讲不出来。
我们在老“皇宫”待了半年,就搬到位于东风大街的53栋,上面有个小角楼,是设计处办公室。我们搬到了昆仑路96栋居住,生活条件好了很多,有暖气,也有热水。
刚搬回来时,工地还没完全建成,厂房也没建完,我们就到工地干活。苏联有个义务星期六,我们跟着苏联学,积极参加劳动。共青团花园和汽车工人俱乐部就是靠大家的义务劳动建成的,反映了建厂时一汽人的精神面貌。
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制造出来后,要由设计处道路试验室做汽车道路试验,测试汽车性能是不是达到技术标准。做试验要有试验道、车道、跑道,也要有直线路段。直线路段约一公里,全加起来至少三公里长。
当时没有试验条件,就在长春市南湖附近找了一条路,在土石路上做试验。做试验时,两边站着警察,不让其他汽车经过。常规试验做了很多,均达标了。
这时,不知是谁建议,说要做一次破坏性试验,看汽车能不能抗震,总厂采纳了这个意见。破坏性试验不是常规试验,就选了废弃的、坑坑洼洼的西四环路中的一段。试车司机头戴坦克帽,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行驶。行驶结束后,检查有没有地方破裂,做好记录,当作之后汽车改进的依据。
解放车刚投产时,孟少农就提出建议:一是把驾驶室缩短,加大载货面积;二是要做解放牌改装车或者变型车,如用解放牌底盘做公共汽车和客车。最重要的是,解放车产出后,要立即做牵引车和翻斗车,当时牵引车可载货20多吨,中国要搞建设,需要大量翻斗车。
1956年,时任一汽副总工程师孟少农找设计处商量。他说,解放牌要做改装,要为翻斗车和牵引车做准备。当时改装车在社会上并不多见,而且解放投产还不到一年,还需要改进。更多人想的是好好干,把产量提高。所以,我一直佩服孟少农,他真是学术泰斗。
在孟少农的领导下,设计处提出产品规划。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一张A4纸,纸上有个表,列着几项任务:一是解放要做变型车,包括牵引车和翻斗车,还要做公共汽车,同时提出,解放牌要换型。二是要改进解放汽车,消除三大缺陷,通过做试验,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解放牌汽车,这是当时的说法。三是要做中级轿车。四是要做高级轿车。
这个规划了不起,别看只是一张纸,但一汽后来就是走的这样一条路。一汽的产品改造,改的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这些内容。
针对孟少农提出的把驾驶室改短的建议,苏联专家说过一句话——解放牌驾驶室一毫米都不能缩短。因为解放牌车身靠主模型,这个主模型是模子的基础,模具制造都靠它,动一毫米,主模型就要动,装配也得跟着动。
从技术层面讲,苏联专家的说法是正确的。孟少农跟苏联专家商量后,还是决定缩短驾驶室,加长车厢,但这样一来,驾驶室就得重新做主模型,需要做一个全新的驾驶室。
解放准备换型总厂也知道,但没有变成一汽的总厂规划,只是设计处的设计工作规划。设计处做了油泥模型,准备根据油泥模型用红木做主模型。苏联除了提供图纸资料,还把复制的一个主模型给我们,做解放牌车身。
主模型专门存放在一个房间里。它对环境要求很高,气温和湿度都要在一些范围内才行,修改也要依规定程序。主模型是做汽车冲模的依据,冲出来的模型要跟主模型形状相对。但是很可惜,这个主模型一天都没用过,相当于白费。
为什么没用上?外人可能不完全知道。解放牌投产时,很多零件来自苏联,但因为模具在生产的全部过程中有磨损,做出来的汽车零件不符合原来的主模型。如果再按照这一个主模型做,将来零件肯定装不上,装第一辆解放汽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产品规划里提到做轿车,但那时候谁敢搞轿车?想都不敢想。1957年,一机部部长黄敬到一汽考察,召开座谈会时,他就问一汽何时能做轿车,如果做轿车,有什么困难。
做轿车可不简单。一汽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轿车是怎样的,大家没有实际体验,对轿车知之甚少,需要有样车,而一汽一辆样车都没有。二是一汽这些技术员都是做卡车出身的,卡车刚投产,还有大量设计更改需求,目前设计处没这么多人去做轿车。三是工程大楼面积不够,设计处只有试制两辆解放牌卡车的能力,要做轿车,试制面积不够。
黄敬部长当场对这样一些问题做了安排。他说:“样车我负责,你们看中哪款车,我负责调。至于人员和工作大楼问题,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
当时全国汽车方面的技术人才都集中在一汽。一汽决定,把吴敬业、刘炳南、史汝楫、富侠这四人调过来充实设计处。吴敬业为处长,刘炳南、史汝楫为副处长,陈全是总支书记。
这时,解放牌卡车的生产准备和调试工作已基本结束,一汽又将车厢厂技术科科长王敬仪、总装车间技术科科长庄群等技术骨干抽调到设计处。那些参加工作不到半年,但熟悉加工工艺的大学生也被抽调出来。
办公楼问题好解决。我们在两层楼的工程大楼上增建了三楼,又想办法在试制车间外搭建了小棚子。
黄敬回北京后,立刻调来了美国福特ZEPHER、法国SIMCA、日本丰田、德国奔驰190,还把法国送给周恩来总理的雷诺和朱德总司令的捷克斯柯达也调来设计处当样车。
一汽领导下令,轿车要按照“仿造为主、自主设计”的方针来做。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可以仿造样车,还没有自己设计的能力。大家开始动手拆样车,接着做选型,在1958年做出了东风和红旗。
接着讲改进解放。改进解放卡车时没有主模型,就靠油泥模型做车身,再根据油泥模型手工敲零件,做出汽车形状,这就是解放CA11A。
改进型解放车设计完后,设计处从上到下开始紧锣密鼓地试制CA11A。1958年年初,CA11A试制成功。
相较于解放CA10,CA11A做了较多改进,改动了底盘上的主要零部件,如将后桥改成单级后桥,悬挂和转向都有改动。CA11A不叫换型,叫大型现代化,又称为练兵,是为解放线年,一汽又提出要做解放改型,在解放CA11A的基础上做了CA11B。CA11B的车头和底盘做了更多改进,原来95匹的发动机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于是又加大了发动机的马力。
接着就是“”,大炼钢铁。我在这时得了肝炎,因为怕传染,不能跟外界接触,就待在家里,直到1961年才恢复工作。
1962年,上面安排我担任军用越野车主管设计师,开始着手解放越野车的改进工作,最后定下来的车型是解放CA30A。后来一汽越野车分厂投产,CA30A成为大批装备部队的主力车型。
1964年“四清”结束后,我由设计处科长提升为设计处副处长,主要领导解放换代产品的开发,以及制造解放变型车的工作。
解放新产品做得也不少,如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了60吨矿用自卸车,用来开发矿业。解放还做过面包车CA630,做过吉普车CA230。
解放CA140做了又否,否了又做。因为没投资,生产也没条件。这些工作就一轮一轮地做,反反复复地做,其实都是做虚功,解放也一直没换型。二汽东风140投产后,解放越来越落后。东风140原型车就是解放CA140,他们拿去后做了改进,在市场上卖得很火。
1969年,我被下放到车间劳动,1971年回到设计处。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说,有个出国任务要我准备一下,去英国。我非常好奇出国去干什么?
这次出国是一机部组织的,由刘守华带队,一同出国的还有孟少农、冯克和中国重汽的人,我们组成了一个较大的访问团。出国前要进行政治学习,代表团集中在汽车局学政治,学完后还要讨论,我就偷偷学英语,结果出国后还真派上了用场。我们在英国收集了好多卡车资料,为解放换型做准备。
后来听一位国家领导人说:“解放一直不换型……一汽也不争气。”一汽其实挺冤枉的。我们做过很多换型准备,也对很多地方做了改进,如从CA140改为CA15,加大发动机马力,载重吨位从4吨改为5吨……设计处大概做了1000多项改进建议,但还是赶不上东风。
日本有一个代表团到一汽参观。参观后,刘守华和李刚请他们评价一汽生产。他们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没有评价。后来,他们说,“你们到日本去看看”。
1978年,约20个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代表团去日本考察,由刘守华和李刚带队。我是设计处代表。在去北京的火车上,刘守华对我说,汽车局批准我担任一汽总设计师。因此,到日本考察,我是以一汽总设计师的身份去的,同时也是设计处处长。
我们在日本考察了半年,参观了几个大公司,感觉差距确实很大。日本汽车质量已经提升很多。一汽刚投产时,曾在北京办过一次汽车展览会,日本三菱公司也来参展。说实在话,当时解放牌汽车跟日本车相比,不是太落后。但这次去日本一看,他们汽车质量提高不少,解放车已经和人家不在一个档次上,更加凸显解放换型的紧迫性。
在日本考察的这半年,我一直在寻找双方差距。从产品设计方面找不到答案,就从技术方面找,我收集了很多设计资料和试验室资料。我记得去丰田公司考察时,他们不愿意我们参观他们的设计部门,对我们严格保密,我们做了大量疏通工作才进去。
后来解放换型,有些技术方面的改进也参考了日本的汽车。一是车身设计。日野汽车的车头可以翻开,便于保养,我认为解放换型可以借鉴。
二是发动机。日本的车都用柴油机,而国内用的是汽油机。考察前,设计处就确定目标,要参照用柴油机的车型,结果看中了三菱6D14,它在功率、尺寸各方面都符合解放换型车,所以我们当场就确定要把这套技术移植过来。
三是离合器。确定用英国的离合器。这些设备都是准备在解放CA140(后来变成CA141项目)换型时使用。
有一天,我突然开窍,觉得设计有差距的最终的原因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体制。当时,日本是市场经济,我们还是计划经济,国家统收统支,企业拿不到钱,利润留存太少,无法自行进行产品研制。而且国家统购统销,一汽不管销售,也没有市场概念。一汽和解放的落后,跟这一些因素都有关。
我记得日本社长给我们作报告时就说:“市场之间的竞争很激烈,产品必须一直在改进,不断换型,才能活下去。”然后,他问刘守华:“你们中国怎么样?”
日本社长说:“我实在羡慕中国,在中国当社长不用愁,你们有铁饭碗,没有市场。”
回一汽后,领导让我们在全厂作报告。我就讲,解放不换型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市场之间的竞争,计划经济的统购包销、统收统支的政策使换型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当时中国还没有市场经济概念,但已经有市场经济苗头。
后来,我跟刘守华建议。我说,日本设计机构机制跟我们完全不同,它叫主查制,没有总设计师,也没有设计处,总厂给每个进入市场的汽车品牌设定一位主查,就管车型,总厂设主查室。打个比方,解放牌汽车设定一个解放主查,主要负责了解市场对解放的需求,根据销售部门反馈回来的改进意见进行产品改进和换型。
主查一旦经董事会通过后,就代表总厂管理各项生产事务,包括何时出产品、何时完成改进项目、何时进行换型、换型用什么技术,都要在规划表里提前统筹,这是以市场为目标。我主张在解放牌换型时推行主查制,这件事情我建议了很多次,都没成功。
一汽一直想摘掉“30年一贯制”的帽子。李刚担任厂长期间,由他带队到北京各部委去游说,希望上面支持解放牌换型。我们说,不花国家的钱,就用一汽节省下来的7000万元作为换型资金,即使这样也没能得到上面的同意。国家当时要支持二汽建设,不同意一汽换型。
有一次,我们到向作汇报,他当时是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我们在北京待了78天,我画好解放CA141结构图后,在旅馆里做好幻灯片,准备在汇报当天放映。当时国内幻灯机不多,我们用的是日本送给中国代表团的礼物。
汇报当天,幻灯机接头和会议室用的接头对不上。我急中生智,用解放公司的纪念品——螺丝刀,把幻灯机接头拆下来,换上能去的接头。结果刚换完,就出现了。我们给他作完汇报后,他同意我们用一汽积累的资金换型。
耿昭杰接班后,一汽用这笔钱,再加上国家拨款,开始做解放换型。大年初六,耿昭杰带着大家在一号门开万人动员大会,说一汽要背水一战,破釜沉舟,搞解放牌换型。这次会议当时很有名,是一汽第二次创业的标志。
解放CA141投产后,出现了很多质量上的问题,特别是发动机问题。配套产品也有很多问题,我分管配套工作,为稳定质量做了大量攻关工作。
1995年,我65岁,从一汽退休。我这一辈子都在做解放,对解放很有感情,但最后就留下一个遗憾,就是前面我提到的产品机制,应该学日本推行主查制。

一汽换型时,全厂就一个产品,确实不太需要主查。但后来实行多品种生产,就应该推行主查制,把市场跟生产、产品连成一条线,效率才会高。这个事我推了很多年,从刘守华担任厂长时就开始推,直到我退休后,每年跟集团领导见面,我还会提这个建议,但都没有实行,非常遗憾。
展望一汽的发展之路,应当将一汽精神发扬光大。总结一汽精神,我认为有以下几条:一是誓夺第一,勇创新业。二是群情激昂,艰苦奋战。三是博采众长,自主发展。四是科技领先,勤奋学习。